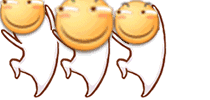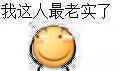原载于社群杂志《方圆》2023年11月刊。发布于2023年11月20日。
早在二二年五月,这篇随笔的草稿就打好了。但那篇草稿读起来感觉比较奇怪,所以我就把它悄悄藏起来了。时隔一年半,我又把那篇草稿拿了出来,下定决心重写一遍,权当《方圆》创刊两年来的回忆。
在正文之前,我想先说说这篇文章的标题。去年春天,我在一本杂志上的一篇散文里看到了一个叫《我在成都当诗歌少女的经历》的标题,但那篇散文仅仅作了引用,并没有过多介绍。后来我在网上找到了原文,作者是马雁。我很喜欢这个标题,所以换了两个词之后就拿过来用了,但改过的标题似乎比原题少了点感觉,好在我只是想写点碎碎念,所以标题起的不好应该也没关系。
二〇二二年一月,我在《方圆》发表了创刊词《依方寸之土地,仰圆穹之星辰》。我在那篇创刊词里阐述了《方圆》杂志名的含义和刊物的核心目标。那时我刚刚来到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,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让我自由支配。那几个月我所读的字数相当于以前的所有阅读量的总和,几乎什么样的书我都可以读下去,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获得非任务型阅读的机会。
两年前的二一年冬月的某天,我正在对着屏幕上的《〇》报发呆。突然一个想法在脑海里浮现出来,于是,《方圆》出现了。那时还是《莉亚晚报(非日常刊)》,后来我们对外征集了新刊物的正式名称,但并没有令我很满意的,所以就自己琢磨了一个出来。新刊物出版后,Aunst给《方圆》设计了2022版版面样式,而Arthals 则为本刊设计了Logo,并沿用至今(就是封面上期号右边的那个)。就这样,在二〇二二年元旦的第二天,《方圆》向大家第一次问了好。
主持报社工作给我的影响有很多,但它们大多都可以概括成两个方面——认识了更多的人以及获得了更多的能力。《莉亚晚报》有一个随机tp的小板块,有许多朋友都接受过我的随机采访。《莉亚晚报》的随机采访、二二年四月的新人引导以及后来在文旅社任导游,这些经历都让我认识了更多的朋友。今年夏天,我学着单项式的样子给我的一些在网上认识的朋友寄去了明信片。虽然我写的字一言难尽,但似乎每位收到我明信片的朋友都很开心,这种打破次元壁的感觉真的很奇妙,以后会不会开展类似的读者活动也说不定。
至于获得了更多的本领,最直接的应该就是增长了写作的能力。不敢说自己的文笔有多不坏,但做起语文试卷的语言文字应用题倒是比两年前更加得心应手了。翻开早期的《方圆》,过去的我写下的文字令现在的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。这两年来我的写作水平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也不好说,但写到这里,我突然想起来单项式在因式分解开栏语中所说的那样:“表达的能力并不是天生的,它需要打磨,需要练习,而唯一的练习方式,只有多写。”
重要的在于将自己寻思的东西写出来,而且一些语言只有在写出来后才会发现不对劲的地方。只有把内在的思绪转化为外在的文字,思绪才能被冠以思维之名。在写作之外,我还学了点Adobe Id和github的使用方法,非常感谢曾在任何方面指导过我的朋友们。在上海作家协会主办的《萌芽》杂志的封底上,有这样一句话:“真实的载体方可承载真实的力量”。我想,在漂浮于信息之海之上的赛博世界,像《方圆》这样的期刊应该可以被称为“真实的载体”,进而可以承载突破次元壁的真实力量。新冠疫情爆发后,“元宇宙”的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,但是“元宇宙”究竟能给人们带来什么仍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。网络的发展让线上世界成为了人们的第二故乡,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的“元宇宙”会将互联网在精神寄托方面的属性大大加深。但当人们在虚拟空间拥有真实的虚拟身体后,现还能不能被称为现实,还是说“元宇宙”内部会重新具备现实世界的所有特征,这些问题我们至今都没有弄明白。
但就目前来说,线上世界确实可以替代一部分现实中的情感需要,特别是在像这样的后疫情时代。《莉亚十日报》第一期开刊语中关于废墟之下的坚桌的比喻,放在这里应该也一样适用。
好像写了很多话了,就此停笔吧。感谢你可以看到这里,晚安,祝好梦。
三零于二〇二三年十月廿八日凌晨一时 时窗外明月高挂,远处楼房窗灯闪烁